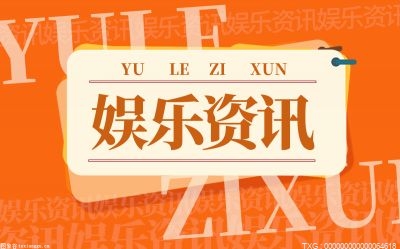在《万里归途》中看见张译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
过去几年,他在大荧幕上演绎了许多象征“使命”与“责任”的角色,虽有相似,但仔细看来又各有不同。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用张艺谋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好演员的本事,能将同类角色表现得各有千秋,“张译,很难得”。
近几年所有和张译合作过的人,在评价其时都会说,他是一个“你要什么就能给你什么的演员”,但轮到当事人形容自己,他却说自己只是一个“还算可以”的演员,低调得可以。
在演艺圈里,张译如同一个“隐匿者”,除了演戏,他几乎不会以任何一种形式招揽众人的目光。
在生活里同样如此,他有很多不常规的“爱好”。
比如,在闲暇时将一切能折叠的东西都叠成豆腐块,哪怕只是手边的一块抹布;把硬盘里的所有电影按照国别、导演、所获奖项仔细分类,方便日后检索观看;手机里的所有app不仅要按照功能排列,每个类别的app图标还要遵循飞机对飞机头、火车对火车头的原则整齐摆放在手机屏幕上……
他的习惯都是“规规矩矩”的,如果一一列举出来,还有些严苛和琐碎。
如果你不熟悉他,会觉得这个人奇怪且麻烦;可若将细节剖开来看,那一切就显得合理起来——
他过往的44年人生,其实都藏在里面。
张译当过9年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走投无路时,是部队好心收留了他。
1997年,19岁的他从东北到北京考学,本想去念表演院校,但因为种种原因,他考了几次,全部落榜。
打道回府前,他听说军区战友文工团正在招演员,抱着“最后一搏”的心态,他去了,考完试回家等了半年才等来一张“自费生”的录取通知书,他就这样进了部队,成为了一名话剧团学员。
军队讲究纪律,一切行动的准则都是“服从命令,整齐划一”。有很长一段时间,张译都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他不理解,大家都是活生生的人,为什么非要做到“一模一样”?
适应规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对于刚入伍的张译来讲,那简直是折磨。
他打小就有一个“坏毛病”,不爱吃饭。在新兵连时他特别挑食,每回吃饭都会剩下一些,部队明令禁止不让浪费粮食,他就偷偷将剩饭倒进垃圾桶里。
有一次他倒饭被队长逮个正着,全队都因此被罚站军姿。队长告诉他,如果不把倒掉的饭菜吃掉,那大家就要一直在大太阳下站着。没办法,他只能当着全队战士的面,将刚刚扔掉的饭菜又捡回来、吃进肚子。
张译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一气之下想到了自杀。那一天,他先是在三楼的宿舍走廊里徘徊,窗下是灌木丛,跳下去也不会怎样。那向更高处走呢?他的军衔不够,无权爬上高楼,最终“自杀”一事只能不了了之。
“规则”曾让张译愤怒,但在关键时刻也救了他一命,他也是在很久之后才明白的,“部队里的训练和条令,就是为了要打掉个体的自由散漫,这样‘整体’才能形成”。
张译在部队当兵
当“整齐划一”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张译也渐渐变为组成“规则”的人。他曾在自传里讲过一件“丑闻”:
刚当兵那会儿,部队不允许军人使用私有通讯器材,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张译都没有手机。在那个年代,拥有一部手机可以代表许多,他向往过,但因为兜里没钱,梦想一直没能成真。
某一年年底,张译放假外出置办年货,在返回部队的路上,他看见街边躺着一款时下最新款的手机。
捡还是不捡?他为此纠结了许久,最后藏在皮袍底下的“小我”打败了原则,他飞速抓起手机揣进兜里,然后乘着出租车扬长而去。
带着捡来的手机回了部队,张译接连几天都寝食难安。被领导发现了怎么办?如何解释手机的来历?是不是可以把它埋进地里?可是部队用铲子也需要申请……
因为一部白捡的手机,张译日日提心吊胆。某天队长突然到宿舍检查内务,手机在慌乱中掉到了床下,零件稀里哗啦地摔了一地,就在此时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捡来的根本不是手机,而是一部已经坏了的计算器。
那一刻,张译猛然感受到了解脱,想起为此担惊受怕的日子,他一度以为,这是老天给予自己重新做人的机会。
张译与手机
引以为戒,后来的张译时常会想起这件事,就像是一种提醒,告诫他千万不要做出格的事。
这种“本分”组成了他性格和行为中的一部分,并在其脑海中形成了一套顽固的价值观与方法论。
所以他有时是迟钝的,举一个极为简单的例子,那就是出道至今,除了一些必须要参加的电影宣传活动,他近乎回绝了所有娱乐综艺类节目的邀约。
他反复强调自己是演员不是明星,有人将这种自我定位解读为“职业清高”,但张译的本意,其实是对自身能力的不自信,或者,是谦逊。
能够成为一名娱乐大众的流量明星是一种本领,但他自认并不具备这项能力。
部队和他出道的年代没有教会他这个,于是他至今也不想走进这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谈起不懂娱乐的自己,他甚至是自卑的。
与他同期成名的演员王宝强、李晨、陈思诚等人,都或多或少地在娱乐圈里开辟出了另一条道路,唯独他一直执拗地在演员这条路上耕耘。
问他有没有想法做导演?他说,演员还没做好,不敢想别的。
那怎么不参加综艺赚钱呢?他答:“不会那个”。
张译坦言,自己至今都无法适应“圈里”的追捧和夸奖,每当听到众人的欢呼和呐喊,他都会下意识地在心里告诉自己:
别想太多,那不是真的。
在不需要演戏的日子里,张译喜欢将更多时间放在写日记和整理东西上,理顺琐碎的文字和细节,总能帮助他看清并不完美的自己。
在日记里,张译时常会记录一些自己遇到的九死一生的时刻。
记得拍电视剧《生死线》杀青戏时,他要拍摄一个跳海的镜头。摄像机被支在岸边的礁石上,他则随着橡皮艇一起去到了距离海岸百米远的海域。
正赶上退潮,海水不算深,导演一声令下,张译利落入水,不想却踩进了细软的淤泥里。为了保暖,张译全身都被缠上了保鲜膜,四肢关节都打不了弯,无法划水的他感觉自己越陷越深。
他拼命大声呼喊,但因为距离太远,岸上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听见他的求救。几秒钟之后,海水没过了他的嘴、鼻子、眼睛,头顶……
周围安静得可怕,只有海水不断冲击耳膜的声音。隐约可以听见有船划来,但是不能确定,除了下沉,什么都做不了。
平静中,他想起了很多事,一些和现在一样,沉在水底,险些无法上岸的往事。
张译并不是一个幸运的人。
小时候他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但前后两次报考广播学院,全都竹篮打水一场空。为了一纸大专文凭,他心不甘情不愿地自费进入了哈尔滨话剧团,此后整整半年他都郁郁寡欢,每每想起自己未竟的主持梦,他都难受得肝颤。
1996年冬天,全国举行文艺调演活动,团里演话剧,张译闲得无聊便去看了两场,结果被感动得泪流满面,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舞台与戏剧的魅力。
这天之后,张译爱上了话剧。那时话剧团里有一间类似“藏宝阁”的图书室,里面放着团里多年来的经典剧目,明里借不来,他便每天裹着军大衣窝在角落里偷着看,什么时候读完,什么时候心里才算舒坦。
《士兵突击》的编剧兰晓龙曾和张译一同在战友话剧团工作,他始终记得,张译曾在一个大雪天跑到他家,只为借一本前苏联作家盖利曼写的话剧剧本。
张译不好意思“霸占”他人的收藏太久,于是便花钱将厚厚的一本作品全都复印了下来。兰晓龙知道后震惊了好一会儿,因为在他看来,那本不是什么知名著作,可张译还是极为虔诚地拜读了剧本里的每一个字。
在哈尔滨话剧团时,张译前前后后阅读了超过2000个剧本,到了今天,他话剧剧本的收藏量在四五千册。老师看出了他的喜欢,便告诉他想看好话剧那得去北京。
于是第二年,张译便背着行李做起了“北漂”。初进京时他雄心勃勃,理想是考入一流的表演院校。结果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因为体检不合格,他连主考官的面都没见上;面试中戏,老师又觉得他“颜值”不达标,直接建议他去念中文系或者导演系。
一波三折后,他进了战友话剧团,本以为可以守得云开,不想却走入了另一种无奈。
在战友话剧团时,张译是全团老师公认“最不会演戏的人”。话剧《士兵突击》的导演、表演老师彭澎第一次见到张译时便觉得“这孩子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一看就不是当演员的料”。
在团里,张译是彭老师打得最多的学生,但打是亲,骂是爱,师徒二人从来没为此红过脸。相反的,他知道,彭老师其实是全团最保护自己的人。就像在多年以后的《士兵突击》中,他对许三多那样。
张译(左)与战友合影
张译天生就瘦,但彭老师不知道,一直担心他是营养不良。在部队时,老师常常借着打扫卫生的名义,把张译叫到家里吃饭、看碟片、研究最新的电影。
张译跑了好几年的“龙套”,团里不看好张译,每回演出都给他安排幕后工作,只有彭老师会跳出来和领导据理力争,说张译才是那个最应该站在舞台中央的人。
但彭老师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张译依旧是团里最不起眼的存在。
从学员转正后,与他同期进团的兄弟都已经演上了主角,唯独他还在舞台上扮演路人1、尸体A、士兵甲,一场剧目几个小时,他被分到的台词一般不会超过10个字。
有一年团里要拍一部电视剧,外聘的女导演点名要张译演男三号。张译知道后高兴得“如梦如幻、欲仙欲死”,为此还特意推了另一个剧组的邀约。
当天夜里,团里开大会,张译以为是要公布选角名单,特意选择了后排的位置坐下,想低调一点,不成想团首长在会议上宣布的第一个消息,就是剧组解散了,因为“选错了导演”。
领导在会上说,团里看上的演员,女导演一个都没用,偏偏挑了几个最不会演戏的。听了这话,张译脸涨得通红,他不敢抬头,生怕对上别人打量的目光:“当时剧组在我们团只选了我一个演员,领导就是数落我呢。”
张译在部队参加节目录制
张译还有一位恩师,外号“五大爷”,退伍前,他把大伙凑在一起吃了顿饭,席间老师喝高了,揽着爱徒的肩膀声泪俱下地说:
“译啊,五大爷就爱你啊,你是个好孩子啊,但是可不敢再演戏了,你演戏就是个死啊!”
老师说得诚恳,张译只能含泪点头,但演员有那么多,为什么就不能是自己呢?他一直也没想明白。
不被肯定的日子过了6、7年,张译自己也有些疲惫了。2003年前后,已经25岁的他琢磨着转行,从演员变成了编剧,他不断向各方投稿,但得到的回应少之又少。
有一次某个剧组破天荒地找上了张译,希望他能尽快出一个20集的电视剧本。张译激动得不行,连定金都没收,就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万字,眼看着就剩最后两集了,剧组来电,先是道歉,紧接着就说投资方撤资,戏黄了,剧本也不要了——又白忙活了。
有那么几年的时间,张译绝口不提演戏的事儿,也不是不想,只是每次讲起,心里都会隐隐作痛。
那时候彭澎老师已经不在一线教学了,听说张译“转行”了,他主动找上了学生,二人聊了许久。很多年之后张译仍记得谈话的内容,他说,要不是因为彭老师的鼓励,自己可能真就放弃演戏了。
2015年,37岁的张译凭借电影 《亲爱的》韩德忠一角,获得了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从艺19年,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专业性大奖。
在上台发表获奖感言时,张译一口气说了17个“感谢”,其中有一个便是“感谢我的表演老师彭澎”。
金鸡奖典礼结束后不久,彭澎生病入院,张译去探望,进了病房,他像过去一样嬉皮笑脸地开玩笑,但在看到老师术后的伤口后,他还是没忍住,躲在医院走廊里哭了一鼻子。
离开医院前,张译把金鸡奖的奖金偷偷留给了彭澎的妻子。彭澎知道后没有说话,只是用笔在装钱的信封上写下“张译的奖金”,然后放进抽屉里,一直到出院也没舍得用。
张译与彭澎老师
张译入伍时是冬天,新兵连长途拉练,大家都累得不行,唯独他日日精神抖擞。当时他主动担当起了扛军旗的工作,连长听说后悄悄和队长说:“这孩子不错,但是你记着,将来养不住。”
彼时,张译认为连长话说得奇怪,他想,部队就是自己的全部,要把毕生都交给这里。但在2006年,他再想起这句话,又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冥冥中注定。
这一年,他出演了《士兵突击》,扮演史今班长,戏份不多,却足以帮助他名声在外。
也是在这一年,28岁的他,从“一个兵”变成了“一名影视演员”。
张译《士兵突击》史今班长
张译和《士兵突击》的缘分始于2001年。彼时,《士兵突击》还是一场名为《爱尔纳·突击》的话剧。张译参与其中,是场记、画外音、群众演员、监狱警察扮演者,以及袁朗B角。
说是B角,但团里并不信任张译的能力,袁朗A角因故不能演出,团里宁愿找别人替补,也不会让他上台。
可张译深深爱着这场话剧,有关它的每一个细节,他都如数家珍。他可以熟记每一个人的每一句台词,连场上的灯光、道具、音乐、布景的切换程序都烂熟于心。
每次演出、排练结束后,他都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待人群散去后,他会将礼堂的大门从里面反锁,然后守着空荡荡的观众席将整场剧再从头到尾演一遍。
他不敢开灯,生怕被人发现。偌大的舞台漆黑一片,他看不见前方,也听不见掌声,除了自己声音的回响,得不到任何回应。无数次,他幻想,有朝一日也能在《突击》中出演个角色,哪怕只是一个配角。
张译在“战友”出演话剧《爱尔纳·突击》
只有一句台词:“你的时间到了。”
2005年,电视剧《士兵突击》开始选角,张译得知后给导演康洪雷写了一封3000字的自荐信,里面详细列举了自己的优点与缺点,讲明了自己渴望出演许三多的心愿。
自荐信送出的当天傍晚,张译便接到了剧组的电话,副导演告诉他许三多有人选了,如果他愿意,可以出演班长史今。
没有任何犹豫,张译答应了,可电视剧拍摄时间正好撞上了战友话剧团的演出时间,两者只能选其一,最终他选择向部队递交了转业申请。
团首长为此火冒三丈,拍着桌子问张译:“部队培养你这么多年,你说走就走了?!”
张译也难过,低着头半晌不说话。转业意味着什么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离开部队当演员,有可能扬名立万,可更大的可能性是一无所有,弊大于利。
“但我还是觉得,该换换了”。
张译当兵的最后一张照片
《士兵突击》中史今班长退伍的戏,是全剧组的杀青戏,正式拍摄前,张译恰好接到了部队的电话,转业申请通过了。
挂掉电话,走进片场,摄像开机,想想当兵的9年,张译为全剧奉献了“最感人的片段之一”,没有演技,全是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