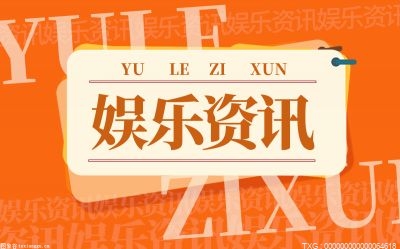确认关系4个月后,46岁的余秀华和32岁的杨槠策拍了婚纱照。
从两人公开的视频来看,一起拍照的还有双方父母以及杨槠策的女儿,视频被打上“家和万事兴”的标语,但“结婚”这层窗户纸,余秀华始终没有向外界捅破,在社交平台上她仅仅将这件事定义为“拍婚纱照”,释放出无限遐想空间。
作为擅长谈论爱情的诗人,她曾不止一次表露出对婚姻的抗拒和对爱情的无望,“如果谁现在说想和我结婚,我会撒腿就跑,害怕婚姻”,但她依然鲜活地投入到这段感情中。她身上有天然的冲破框架的能力,即使这框架是由自己搭建,也在所不惜。
过去8年,世俗意义上的条条框框在她面前土崩瓦解,而她的人生也从未停止发生巨变,就像她在公开婚纱照视频时所写的文案:
爱是谜,人生的过程也是。
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
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
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
我们走到了外婆屋后
才想起,她已经死去多年
——《我养的狗,叫小巫》(收录于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
这首诗是余秀华成名前的作品,被收录于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广为流传。诗中的“小巫”,是她曾经的一只狗。那狗非常听话,对它说去谷堆,它就去谷堆趴一晚上。后来,它被人打死。
而诗中的“他”,则是指余秀华的前夫,尹世平。由于诗里的意象,很多人以为她常年承受家暴。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将“余秀华”和“家暴”联系起来的文章见诸网络。但事实上,余秀华说他只动手过一两次,也没有磕墙那么严重。“他不敢。我跟他讲过,你再敢动我一指头,我就把你干掉!”
她并不打算借机往前夫身上泼脏水,因为揪着她的头发往墙上磕的并不是这个男人,而是世俗。
从在清明节出生那天开始,她的人生就被世俗绑架。彼时因为倒产她成为脑瘫,终身残疾,厄运与生俱来。
摇摇晃晃长到19岁,她在父母操办下嫁给了31岁的上门女婿尹世平。当时的她对于婚姻并无概念,也没有抗拒,但如果套用她后来的理论“任何两性关系的本质就是有所图”,便会发现问题所在。
她在诗中写那一段婚姻:“在这人世间你有什么,你说话不清楚,走路不稳/你这个狗屁不是的女人凭什么/凭什么不在我面前低声下气。”
在泥水中匍匐行走,世俗的不平等尽收眼底。有一年,尹世平带着余秀华讨要800元工资。他说,等老板的车开出来,你就拦上去,你是残疾人,他不敢撞你。
余秀华问,如果真撞上来怎么办?尹世平没说话。那时,她就明白,在对方的眼里,自己的生命只值800块钱,还不如一头猪。
离婚的念头在他们结婚的头几年便冒出来了,但余秀华的父母不同意,理由是:“她是残疾人,老公是健全人。”
父母为余秀华所图的是安稳余生,但余秀华真正所图的是精神世界。“我老公看见我写诗他觉得烦,我看见他坐在那里我也觉得烦,互相看着都很不顺眼。”
她讨厌自己摔跤时丈夫脸上的笑意,讨厌他被烟卷渍黄的手指, 面对不幸的婚姻,有的农村女人会选择拧开农药盖子,比如余秀华的小姨,但余秀华觉得不值得,她选择以诗自度,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
尹世平常年在外打工,很少回家。父母给余秀华开了一间小卖铺,但顾客来了,她也不搭理,一直在埋头写着什么,左手压着右手,颤颤巍巍,笔尖划破小本子,也划破人生。
余秀华的字
《诗刊》编辑刘年记得,2014年一个昏昏欲睡的中午,他正“像地质工作者找矿一样找诗歌”,发现了余秀华的博客。他说,初见这些作品,“就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睡意全无。”
“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刘年写道。
余秀华的出现,搅弄诗坛,《月光落在左手上》作为她的第一本诗集,创造了出版界的一个纪录,从确定选题到下印厂,仅用了9天。
39年岁月在这9天里被集中翻阅、筛选,文字成为印刷体,内容没变,但文字承载的命运齿轮,已然转动。
我爱你。我想抱着你
抱你在人世里被销蚀的肉体
我原谅你为了她们一次次伤害我
因为我爱你
我也有过欲望的盛年,有过身心俱裂的许多夜晚
但是我从未放逐过自己
我要我的身体和心一样干净
尽管这样,并不是为了见到你
——《给你》(收录于诗集《我们爱过又忘记》)
2015年2月,《月光落在左手上》发行,销量很好,至今仍在加印。诗的走红,让她对婚姻的不满在公众面前被不断放大,而版税的到账,也让她将文字中的抗争落到实处。她下决心离婚,打电话叫尹世平回来,“这个月离婚我给15万,晚一个月就只给10万!”
时间被金钱利落划分,那年冬天,她走进法院,向工作人员递上离婚材料。工作人员看了她一眼,走出了办公室。她隐约听到那人在打电话,言谈间有些特别的字眼:“那个诗人。”
拿到离婚证那天,前夫一个劲儿地笑着,余秀华的心情也不错,两人吃了一顿“散伙饭”。 母亲得知女儿离婚的消息,蹲在院子里哭。父亲劝她:“有什么想不通的?是你女儿不要人家,不是人家不要你女儿。”
一年后,她的又一本诗集《我们爱过又忘记》出版,在发布会上,她说起自己的婚姻和四十之惑,甚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云云。
由于身体原因,她的发音很怪,但与她的文字高度吻合,感染力极强,仿佛有一股新生的磅礴之力,她说:“人生中最后悔的一件事,是结婚;而最幸福的一件事,是离婚。”
至于她最想得到的爱情,更早时候她便说:“等下辈子。我不抱任何希望了。”
但她依然渴望爱与被爱。
有人统计过她2014年到2015年1月20日公开面世的诗里面,“爱”字出现了140多次。凭借这些诗,余秀华一夜成名,杨槠策也是在那时第一次阅读她的作品,彼时他还不叫这个名字,而是“杨光伟”,正在辗转各地打工,他赞叹“对方的才华和敢说敢写的勇气”。
两人真正相识,是在余秀华的直播间。彼时,离婚的快乐早已被消耗殆尽,余秀华每天喝酒、直播,“锅底灰抹了自己一脸”。听说余秀华胃疼,杨光伟将自己 的蜂蜜产品寄了过去。
两人加了微信,杨光伟叫她“小鱼”,余秀华说这让她想起自己第一次爱上的人,也是这么叫她。
杨光伟发给她自己写的诗:相遇是一场迟来的告白/我相信缘分/一定是上辈子的记忆/让我今生可以找寻到你/冥冥之中自有注定/前世500次的回眸/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我爱你的文字/我爱你的诗语/我更爱余秀华。
论诗歌,余秀华当然是看不上的,但她喜欢听他说话,所以两人常常视频聊天,时间最长的一次,聊了7个小时。
2021年12月24日,两人第一次见面就确立了恋爱关系。杨槠策回忆:
“当我第一次牵起她的手时,她很紧张,手心都冒汗了,有些不知所措。她害羞得像十七、八岁的少女,而我也像回到了少年时光。”
两天后,是他的生日,余秀华送了他三枚印章。其中一枚就是杨光伟新取的名字:杨槠策。他说:“过去的杨光伟死了,现在的杨槠策重获新生。”
余秀华和杨槠策
几天后的元旦,杨槠策便单方面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他们的恋情,但余秀华迟迟没有说话,因为她无法确定这份感情的性质,以及她对它的态度。
最初余秀华很生气。但后来她想开了:“于我而言,这确实是一份意外。但是一个46岁的女人,还有什么意外不能接受?”
她感谢杨槠策至少没有把她藏起来,他让他的家人都知道了她,让他的同事知道了她,让他的女儿知道了她。这是她所在意的,而网友们的各种猜测和担心,她都不放在心上,她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在他用力爱自己的时候,不停地喊:杨槠策,加油!
余秀华说:“如果有一天他嫌弃我和我分手了,我也会成全他,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的意义,要大于爱情所带来的意义。”
她有凌空的心,不让自己陷入泥泞,也不让他陷入。
余秀华和杨槠策的婚纱照
我们如此悲哀,而又不得不在这样的悲哀上倔强地乐观着。我们很为难,又不得不习惯这样的为难。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沙雕》(收录于散文集《无端欢喜》)
2015年《月亮落在左手上》出版前,余秀华的母亲特意带她到镇上买了一件红色羽绒服。在北京的诗集发布会上,暖气和人气一般火热,但她始终没有脱下羽绒服,红色的毛领被细密的汗水浸湿。直到结束,她都不愿意打开哪怕一颗扣子:“因为里面的衣服不好看。”
3年后,当她的第一部散文集《无端欢喜》出版时,她已经习惯了往返于湖北和北京之间,面对媒体,也应对自如。《无端欢喜》发布会那天,她穿了一条蓝色碎花连衣裙,深V领。当晚,她发了个朋友圈:“一个女人为了检验自己的书好不好,穿了低胸装开发布会,如果人们只看人,就说明书不好。结果没有人看人,她很苦恼,觉得书其实不太重要。”
人和书被放在天平的两端,女人、农民、诗人,三个身份是她苦恼的来源,却又不至于厌弃。因为如果没有“脑瘫”、“贫穷”、“爱情”等充满张力的标签,她或许依然是尹世平的妻子,坐在小卖部里写诗,没有属于她的发布会,没有“诗人余秀华”。
她曾解释过自己为什么没有笔名,因为她写诗从来没想过会出名。在困顿的前半生,她感谢诗歌收留了她。“但是我们不会拿诗歌说事。如同不会拿自己漏雨的房子、无碑的坟墓说事。这样才好。”她依旧住在村庄里,但还是被拽进喧闹的名利场。
成名之后,鄂中深处的村庄里到处印着余秀华的诗,从墙壁到路标,从《穿越大半个中国来睡你》到《给你》,村民们读不懂这些诗,但会称余秀华是“名人”。
村里的外乡人没有停过,从湖北钟祥市贺集乡到余秀华家的一条路,是摩的司机的重要业务,坐在摩托车后座上,出版商、记者、广告商纷纷踏上这片土地。
余秀华一边抱怨虚名已经抛弃了本身,一边写“命运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它终于短暂地把我从横店的泥巴里拔了出来,像报复一样补偿给我曾经梦想的境遇和状态。”
一边无端泪流,一边给散文集取名“无端欢喜”,她说:“无论是无端欢喜,还是无端悲伤,都是源于对生命的热爱。欢喜好像更好一点,不要那么惨兮兮的。”
她为身份标签苦恼,但内心一直有一个明确的排序:女人,农民,诗人。“这个顺序永远不会变,但是如果你们读我诗歌的时候,忘记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尊重你。”
琢磨着他人视角,她又很快转念:“幸亏诗歌最好的作用是为了自己安心。”在她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时,诗歌充当了一根拐杖。她对诗歌是无所求的。
诗人廖伟棠评价余秀华的诗:“放弃辩论,放弃自圆其说,甚至放弃结论,因此与读者并不构成一种咄咄逼人的关系。”
她的诗歌和读者互相需要,她所诉说的痛苦是一群人的痛苦,她的渴望也是许多人的渴望。豆瓣读者说,翻开她的诗,没有路,也是远方。没有风,也会有时光。
了解一位诗人,故事终究只是框架,她的字句才是骨血,读余秀华的诗,才是读她的内心,没有高墙、铜锁和狗,甚至连一道篱笆都没有,可以轻易地就走进去。
一年前,余秀华在为“众声创作者计划”寄语时说:“人间有许多悲伤,我承担的不是全部,这样就很好。”
哀而不伤,是她的人生态度,“苦若深井,倒映月亮”,月光落在她的左手上,清澈一纸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