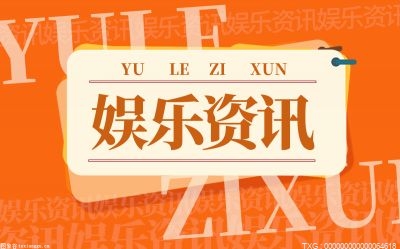作者:阿舒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注定蛰居在家。
早晨设定闹钟抢菜,起的比上学时候还要早,但是一次也没有成功过。倒是辗转找到的跑腿小哥,半夜给我爸妈成功送过鸡蛋和水果。一边等跑腿小哥的消息,一边听京戏,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可以聊以慰藉的兴趣爱好,真的很重要。
戏迷有个毛病,听着听着一上头,摇头晃脑就跟着哼哼起来,叹英雄失势入罗网,哗啦啦打罢了头通鼓,无限春光抱满怀,这才是人生难预料……我最近因为过度气愤怕气出内伤,就拼命听《击鼓骂曹》、《骂王朗》、《义责王魁》、《打严嵩》、《贺后骂殿》。
当然有点阿Q精神。想起十几年前请熊承旭老师给我说《贺后骂殿》的岁月。“骂”是开口音,唱的时候其实是很有难度的,于是愈发佩服程先生,我们祖师爷唱得真是带劲儿啊,爱吃肉的小嘴叭叭叭,骂起来就是贼过瘾!
这几天重读了程砚秋先生青龙桥蛰居务农日记。我的心情和怹老人家差不多,每天担心没吃的,“素瑛来了六天,将我平日所吃的最高待遇白面荞面豆面炸年糕均吃了去了”。
《春闺梦》的有些场景,程先生见过,我也见过。
但我坚信“善恶到头终有报”,程先生说了,“冥冥中有安排”。
无意中看到了这样一段——
虽然我也很想吃20块钱的羊脖子肉,但我更关注上面那一行:王父女来,开始教《探母》。
这里的王父女,指的是王准臣和他的女儿王蕙蘅。
姆们祖师爷这辈子一直不怎么愿意招女学生,新艳秋偷偷“剽学”,把怹气得够呛,大概更加ptsd了,只承认世济奶奶“干女儿”身份,除了解放后的江新蓉和以校长身份教过中华戏校的侯玉兰等少数几位,王蕙蘅小姐可能是程砚秋唯一私人传授的女学生(尽管在日记里,他每次都以“王父女”mark之)。
对于王蕙蘅小姐,程先生还是相当相当够意思的。程派的《探母》和梅派的很不同,白口也讲究,我好几次做梦梦见煮了大肘子求祖师爷说这出,结果被怹老人家重重哼了一声赶出门去。另外,程砚秋日记里好几次提到童芷苓来求学《锁麟囊》,但他并没有答应,根据翁偶虹的记忆,童芷苓是按照王蕙蘅小姐灌制的唱片演的《锁麟囊》——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便是王蕙蘅小姐,这个看起来无比幸运的姑娘,却有一个令人无比唏嘘的结局。
恍惚记得是去年仲春,从上海暂回北京,朋友知我忙碌医院治疗事,贴心约颐和园听鹂馆拍曲。找到停车场停好车,莺啼翠绿,蓦然发现路标竟然写着“青龙桥”三字。
▲程砚秋在家中
青龙桥和颐和园,真的是一墙之隔。1944年,王准臣因为忙中国大戏院谭富英演出胃病发作,经朋友介绍到北京治病,便是住在颐和园荣寿斋。
选择住此地,我觉得主要是为了他的女儿王蕙蘅,王是标准程迷,听说父亲要去北京,要求一同前去,如果能和程先生做邻居,请教起来自然便当。有趣的是,父女二人还没有出发,小报已经哇哩哇啦一顿声张,感觉老程不教也不行了。
程砚秋之所以高看一眼王小姐,大约基于两点,一点因为王小姐的爸爸王准臣是中国大戏院经理。对于程先生的态度,只要看看报上的言论就知道了。
“又程此番张沪得名票王准臣之大捧,王扬言以七千万之钞票人有,给予程伶以实力之支援……上海富商,对于声色之享受,可见一斑矣。”
第二,则是因为王小姐确实聪明好学。
她会西洋音乐,懂乐理,据说曾经把程砚秋四十多出戏全部谱成五线谱,这个“马屁”拍的很准,因为祖师爷本人也很喜欢西洋音乐,《春闺梦》里吸收最多。
她学戏也很认真,下雨也来,认真到老师都有点害怕,我曾经看到日记里有一日不用教戏,程先生那是相当快乐。
她的拿手绝活是学程砚秋打电话。
▲来自王准臣的回忆
王小姐和程砚秋学戏也引起了小报们的关注。我真是佩服那时候的小报,连送三双彩鞋都知道。
王小姐有这样的家庭背景,每次票戏基本都是大佬陪同。比如唱《玉堂春》,王金龙是姜妙香,顺便说一句,这张扮相圆圆脸蛋,倒确实挺像程先生。
被童芷苓拿来作为学习范本的王小姐之《锁麟囊》唱片,题词是梅兰芳。
但王小姐是真的喜爱京剧,喜爱到什么程度呢,爸爸王准臣养病结束之后,回上海去准备程砚秋演出事宜了,王小姐为了学戏继续留在北京,就读于圣心学校(陆小曼曾经求学于此)。后来回到上海,仍旧请程砚秋的胡琴周长华教程派戏,戏迷如此,当算刻苦。
被父亲保护得很好的王蕙蘅一定不知道什么叫“人言可畏”。
所以她可能理解不了,为什么自己在北京求学时,父亲拜托李金鸿和储金鹏作为“左右护法”,连她去北海划船也相伴左右。
进入社交场合,对于一个时髦女性来说,是迷人而又危险的。不幸的是,只会潜心研究程腔的王蕙蘅对于这一点毫无所知。
1948年,王小姐21岁,她的世界里依旧只有程腔。她当然不知道此时上海的物价已经高涨到离谱的地步,根据《 1945 — 1949年中华民国通货膨胀与革命》一文,100元法币的价值在抗战前可以买2头黄牛,到抗战结束只能买2个鸡蛋,1946年只能买1/6块固本肥皂,1947年只可买1只煤球,1948年8月19日只能买0.002416两大米(每斤16两)。
上海乃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如此,经济当然会全面崩溃。一开始,政府打算用抛售物资回收法币的方法控制通胀,谁知物资一抛出,马上被抢购一空,老百姓当然抢不到,获利的都是本地投机商人,还有“消息灵通的南京客人”。
八月流火,一个间接影响了王小姐命运的人来到上海,这个人叫蒋经国。
蒋经国一到上海,立刻慷慨激昂:“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
这场“打老虎”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要打杀威棒,当然要铁面无私出重拳,蒋经国组织“青年服务队”,会同警察局和警备司令部联合执法,开始抓贪腐。
用来祭旗的人中,有一个叫张亚民,淞沪警备司令部经济科长。
选张亚民作靶子非常好,我查过他的信息,他在日本投降之后曾经有过侵占日伪官员住宅的案底,这个人平时性格比较嚣张外露,应该和同事们关系不怎么好。六月底还在抓获投机倒把的张科长在7月15日被捕,9月21日即在上海公开枪毙(之前报纸上还讨论过是否会秘密处决),震惊了整个上海。
但这件事和王小姐有什么关系呢?
皆因这位张亚民去世之前写了一份遗书,遗书上要求太太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两张王蕙蘅照片送还王小姐。
原来,他在死前五个月,1948年的4月认识了王小姐,两人成了朋友。
这两张照片是两人在五月外出游玩时拍摄的。一张是王小姐单人照,一张是二人合影。被捕了随身还带着这两张照片,张亚民肯定是对王小姐有意思,这一点毋容置疑,但我很难理解张此刻的用意,如果对王小姐怀有爱意,托老婆表白,明显是坏到不能再坏的决定,是怎样的脑回路,才让他做出这么蠢的选择。
老婆拿到遗书和照片,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在张亚民被枪毙的当天,包括《申报》在内的大小报纸,都收到了张太太提供的张亚民遗书内容。
▲张亚民付妻遗书
看遗书,这家伙真的还挺擅长写“咯噔文学”的,一口一个“我是为了上海五百万市民生活而牺牲了”“别了人生如梦,想不到我的梦如此短暂”。他让太太把钢笔和两张照片还给“蕙”,《申报》上专门注明这是“张亚明的恋人”,后面还加上一句“使世上多一个了解我的人”——张太太看到要气炸了吧!
“遗书”里只写了“蕙”,并没有暴露王蕙蘅的全名。但之后张太太出辣手大招,她在报上刊登启事,点名“蕙”为王蕙蘅,说不知道王小姐的住址,要求她自己来取遗物。
她同时为张亚民大摆灵堂,居然有许多人前来吊唁送花篮,一时间,小报都盯上了王小姐,还有人守在她家门口,等着看“张亚民的恋人”。我还是以《申报》为例,可以看这篇题为“未亡人語少年得志為聲色所迷,張亞民死於交友不愼”的文章,记者先到新闸路张家,张太太口口声声说张亚民和王小姐是恋爱关系,两人曾经到虹桥玩耍,张曾经要和自己离婚,谁知三天之后即被捕。
王准臣出面解释,说“小孩子懂什么爱情”,并且矢口否认王蕙蘅和张亚民是恋人,坚持称两人是“普通朋友”。
但此时的舆论已经不可控制,世俗流言如同一座座山直逼而来,王小姐这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想起《锁麟囊》中薛湘灵那段“一霎时”,所有的娇嗔都显得徒劳无益,流言成了杀人的刀。
王小姐崩溃了。
10月31日,她吞下四十多片安眠药自杀。11月3日的《申报》,仍旧以“张亚民女友”来称呼她,并且刊登了张亚民给她拍摄的那张照片,照片中,她拿着花朵站立笑着,完全是小女儿神态。
这篇报道刊登后的次日凌晨,王蕙蘅被宣告抢救无效死亡。
据说,王小姐自杀当晚在熟人家中吃饭。有人再次谈起流言,她的回答是:“只能等我死后请人检验我是否处女了!”
她留给父亲王准臣的遗书上说:“人生如戏剧,没想到我唱的竟是短短的程派剧。”
王蕙蘅之死对于老父王准臣的打击是巨大的,我在1948年11月之后再也没有找到有关王准臣的信息,这是他花了多少心血培养起来的独养女儿,却因为卷入一场懵懂的“疑似第三者插足”而失去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王蕙蘅去世之后,小报上还报道了王准臣是做煤矿发迹的,外号“青岛小王”
1949年,王准臣独自一人前往香港。
王蕙蘅的悲剧,究竟要谁来负责呢?
怪她自己天真幼稚?怪父母疏于教养?怪张亚民的愚蠢?怪张太太的恶意传播?好像没有答案。
1980年,须发皆白的王准臣来到北京,当再次见到程夫人果素瑛时,他想起了多年前住在颐和园带着女儿向程砚秋学戏的往事,写下了《小女蕙蘅在青龙桥向程师学艺》。
对于女儿的死,他以一句“受坏人欺骗愤而自尽”“一个很有才能和艺术前途的好孩子,竟因人言可畏,旧社会恶势力的摧残,蒙受不白之冤被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来总结女儿的死因。
又是“人言可畏”,早在王蕙蘅去世后不久,《申报》自由谈栏目就发表过社评,讲王小姐之死和阮玲玉之死相提并论,认为“人言有可怕的杀人的力量”。那些绘声绘色讲述根本不辨真假的王蕙蘅和张亚民约会细节的小报们,那些津津乐道于富家小姐如何失足的看客们,大概早已经忘了,多年前,因为他们的人言,一个女孩在21岁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王蕙蘅去世之后,《申报》“自由谈”栏目发表了一篇题为“人言”的社评,文章将王蕙蘅之死和阮玲玉之死做了比较,说“人言有可怕的杀人的力量”。
王准臣所说的害死女儿的“旧社会恶势力”现在还有吗?
在看过前几天为了200块跑腿费被网暴致死女子的消息之后,我难过到几天不想讲话。我们好像一直对于他人的道德要求特别高,出轨是渣男,要钱是捞女,只给小哥200块是抠门。
在传统媒体缺失、网络媒体又特别发达的今天,我们很容易获得信息,但这个信息并不等于真相,谣言满天飞着,我们确认不了事实,但很容易产生情绪,愤怒的,悲伤的,这种情绪通过语言快速地释放出来,也许只是一瞬间的功夫,键盘敲几个字,噼里啪啦,情绪发泄了,带着点沾沾自喜的道德优越。但那些人大概也不会想到,众口铄金,屏幕那头主人公受到的打击,比凌迟还要痛苦。
在上一篇文章分享了菜饭食谱之后,后台有读者留言指责我是“犬儒主义”,说实话一开始有点震惊,说不生气是假的,但我想了想,没有把这条留言放出来,我不想用自己的这一点点微薄读者影响力,对个人造成语言暴力,我宁可相信,他是善意的提醒,抑或是因为对于现状的愤怒而脱口而出的情绪。对于所有的批评,我愿意报以最大程度的容忍,我也相信,每一位小岁月的读者,都是有着悲悯之心的善良人。
多一份感同身受吧。
王蕙蘅的故事最初是我的实习带教老师、《绝版赏析》制片人柴俊为老师发现的,我亦步亦趋进行了深层挖掘。柴老师有个视频号叫“唱片元音”,上周末我最低落的时候,感谢他为我定制了“杜月笙和他的女人们”专场老唱片直播,老派京剧蹦迪爱好者们可以关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