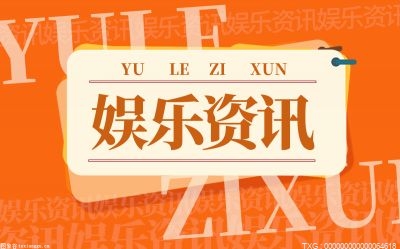近日,作家艾伟的短篇小说集《演唱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唱会》由7个短篇小说构成,是艾伟的最新作品集,出版之前曾在《收获》《花城》《作家》《北京文学》等重要文学杂志发表。这些小说集结了一个个不循常理、如同奇袭的构思,通过“意外事故”破开日常的冰面。
艾伟和毕飞宇、李洱、东西同属于“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上世纪90年代初登上文坛的一批作家,他们一改80年代先锋作家的凌虚蹈空,向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投以敏锐的注视。
艾伟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风和日丽》《爱人同志》《爱人有罪》《越野赛跑》《盛夏》《南方》,小说集《乡村电影》《水上的声音》《小姐们》《战俘》《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等,另有《艾伟作品集》五卷。多部作品译成英、意、德、日、俄等文字出版,在当代文坛享有盛誉。著名文学批评家李敬泽曾这样评价艾伟,“艾伟作为一位小说家,有着巨大的洞察力。”
在《演唱会》中,艾伟真正做到了将自由归还给人物,激发出短篇小说与其篇幅不成正比的无限潜能,展示了短篇小说艺术可以抵达的深度和广度。探照灯2022年1月中外十大小说书单如此推荐《演唱会》:“小说集《演唱会》用七篇有着匕首般锋刃与钻石般棱面的精心之作,向我们展示了短篇小说这一文体在当代中国作家手中所能抵达的渊深宽广。”
《演唱会》的七篇作品分别是《演唱会》《小偷》《在科尔沁草原》《小满》《幸福旅社》《在莫斯科》《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
其中,同名小说《演唱会》是其最新发表的一篇作品。艾伟书写了这样一个故事:“男人”的儿子酷爱周杰伦演唱会,买了黄牛的廉价票却无法入场,于是攀上近旁的摩天轮观看,不料轮盘转动掉下摔死。这里,坑害男人儿子的是黄牛,而吊诡的是,男人自己便是制作假票提供给黄牛的人。《演唱会》聚焦人性的复杂与幽微,既写了破碎生活带给人的创伤,也写出寒夜里的相互慰藉。
《最后一天和另外的某一天》获得了2020年收获文学榜短篇小说榜榜首,书写的是一个女杀人犯的故事。一个女人在监狱里待了整整十七年,成为了监狱里的头号模范犯人。这个女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对这个问题的探寻一直贯穿于阅读体验中。
《小满》叙述了女性母爱本能和身体的关系,曾获得过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代孕的故事,塑造了女主人公小满、古董商人白先生、白太太、女佣喜妹这几个人物形象。
《在科尔沁草原》讲述男女之间不可言说的复杂和暧昧,获2017年《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奖。
另外几篇小说,也都有着对心灵的探索,对人性的揭秘。更为重要的是,艾伟在那些不为人知的角落里,重新发现、拾起我们被偷走的爱与生活。
对话艾伟:
短篇小说是这个正常世界的意外事故

记者:《演唱会》这篇小说的灵感是来自真实事件吗?为何会想到写这样一个故事?
艾伟:有一天我女儿给我讲了一件她童年的事,童年时她和一位小朋友一起去看周杰伦的演出,没买到票,她们进了体育场隔壁的游乐场,在转动的摩天轮上看完了体育场内的演唱会。她说,这是她最难忘最美好的夜晚,回忆起来甚至有一种奇幻之感。又有一天,在一场关于《妇女简史》的读书分享会前,和一位朋友的小孩东拉西凑地闲聊,他突然提起多年前一场演唱会,他买了“黄牛”的假票,进不了体育场。那天,他失望极了,一直在体育场前寻找买假票的“黄牛”,很晚,他母亲才找到他。因为是朋友的小孩,我听了心里有些难受(他倒叙述得相当开心),我突然觉得可以写一个短篇。于是就有了《演唱会》这个短篇。
记者:很好奇如果给故事写另一个版本的结局,会是什么样的呢?
艾伟:在小说世界里我专注人的复杂性,当然故事相当重要,但在讲好故事的同时,我更看重人的复杂性。所以,我没想过另一个结局。你会发现小说和原始素材的差异很大,《演唱会》既写了破碎生活带给人的创伤,也写出寒夜里的相互慰藉。我写了这个生活已经破碎的男人内心的善和恶,最后善微弱地胜出了。我很高兴在小说里保留了我女儿感受过的温暖的气息。我觉得这个故事是敞开的,后面会发生什么我没想过,因此我没有另一个版本的结局。
记者:如果把这个短篇小说拍成时下流行的短视频微电影,男人与男孩,您心目中的演员人选会是谁呢?
艾伟:我对演艺界不是太了解。但你一定要我选的话,我觉得姜武演男人会演得很好,他会把男人的内心的复杂恰到好处地演出来。至于孩子,我觉得应该找一个看起来仁义的愣头愣脑的孩子。
记者:能否简单谈谈您对“短篇小说”这种形式的感受和观点?
艾伟:人是非常容易被观念化的动物。我们脑子里有一些先天的偏见,对某类人怀有根深蒂固的不知道哪里来的固定概念和形象,这构成了我们判断事物的依据。短篇小说或者小说的可贵之处是,在小说世界里,作者塑造一个人物时,他的“个人”的逻辑是高于普遍观念的,小说不对人轻易作出道德判断,不轻易下结论,它试图让人看到比简单的观念更复杂的处境,更难以归类的人类生活。因此短篇小说不是现实生活本身,而是越出现实常规的产物,是这个正常世界的一次意外事故。如果说,小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点用处的话,用处就在这里——小说用具体的“个人”试图去刺穿那个庞大而坚固的观念堡垒,从而可以将活力和可能性归还给生活,将自由归还给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