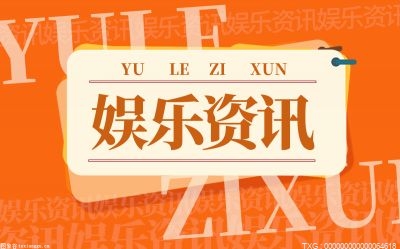12月8日,38岁的邓方树早早来到店里,手机里传来熟悉的声音:“沙县小吃文化节开始了。”抚摸着胸前那个标志性的“吃豆人”商标,他自豪地说:“我们全家都是做沙县小吃的。”
上世纪90年代,邓方树的父亲就走出闽西山区的沙县,天南海北地开过好多店。十几年前,邓方树接过衣钵,继续做沙县小吃。靠着这家“夫妻店”,如今他和妻子在北京扎下了根,还供养了3个孩子上学。
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这样的家庭数以万计。这个原来平平无奇的小县城,逐渐成了“小吃之都”,每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老板,孕育了8.8万家沙县小吃门店,比三大西式快餐巨头麦当劳、肯德基、华莱士的门店数量加起来还多。
知名小吃全国都有,为什么就沙县小吃做成了国民小吃?
“1999年3月4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指出,沙县小吃业的成功之处在于定位准确,填补了低消费的空白,薄利多销,闯出一条路子。现在应当认真进行总结,加强研究和培训,深入挖掘小吃业的拓展空间。”说起习近平同志对沙县小吃的支持推动,沙县县委书记杨兴忠一口气道来,“2000年8月8日,已担任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在夏茂镇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加强以沙县小吃业为支柱的第三产业,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0多年来,沙县经历了5任县委书记,历任县委领导班子牢记习近平同志的嘱托,一任接着一任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坚持把小吃业当作富民强县的重要工作来抓。
全国唯一以政府名义成立的“小吃办”
沙县夏茂镇俞邦村,被称为“沙县小吃第一村”。上世纪80年代,这个村子地少人多、资源稀缺,为争抢田地、水源大打出手的事情时有发生,还有不少人因为赌博负债累累。当时的村支书俞广清很是心焦。
今年70多岁的俞广清回忆,就在大家想脱贫却找不到出路时,有一些勤快的村民一头挑着小煤炉,一头摆着食材,走街串巷,摆起小摊,卖起了逢年过节才吃得上的扁肉(馄饨)、拌面。
上世纪90年代就出去做沙县小吃的村民林英明还记得,小时候天刚蒙蒙亮,他就被隔壁邻居“咚咚咚”捶打肉馅的声音叫醒。一两个小时过后,邻居就挑着扁担摇摇晃晃地出发了,一声声吆喝回荡在沙县的街头。
没人知道谁是第一个出去卖小吃的,但这样的做法“来钱很快”。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这个闽西小城,那些率先走出乡村、进城开店的沙县人,西装革履地回到村里,盖起了新房。到了1997年,夏茂镇回响的是叮叮当当的打铁声,铁匠们日夜赶工,制作煮馄饨、熬高汤的鸳鸯锅。
“最早是穷得实在不行了,老百姓才创造出来这么一个产业。”年逾古稀的黄福松回忆。他在上世纪90年代是沙县副县长,分管农业工作。
但在那个年代,不种地出去卖小吃的仍属“异类”。有乡镇领导担心,如果村民都出去做小吃,土地撂荒了怎么办?俞广清一句话“顶”了回去,“土地少、粮价低,做小吃才有致富的出路”。
当时的沙县县委、县政府主持成立了沙县小吃业发展领导小组,县长兼任组长,下设小吃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这也是全国唯一以政府名义成立的“小吃办”。出身草根的小吃就此成了“全县人的希望”。
此外,沙县政府部门还提出,各个乡镇至少要有一名科级干部停薪留职出去做小吃。当年,“下海”做小吃的干部就有200多人。夏茂镇原党委副书记罗维奎“下海”后,两年多时间里带领乡亲办起18家“罗氏小吃店”。
为推广沙县小吃,这一年沙县政府组织了一场“沙县小吃八闽行”活动,由警车开道,插上彩旗,“沿着国道把福建9个地市全走了一遍”。他们每到一个新地方就停下车,现场制作小吃,顾客免费试吃。每年的12月8日也被确定为“沙县小吃文化节”,传承至今。
走遍一座城,开起一家店
放下锄头柴刀,捡起锅碗饭勺,沙县人就这样开始了小吃生意,打响了自己的口号:“1元进店,2元吃饱,5元吃好。”
接地气,是沙县小吃自带的“基因”。“搭个棚子,支个锅,就开始卖扁肉了。”现做现卖的食品,便宜实惠的价格,让沙县小吃很快在福州、厦门遍地开花。
张万泉是最早出去开小吃店的人之一。1994年,他在福州开起了第一家店,那里靠近一所职业学校和批发市场,是个理想的所在。张万泉骑着老式自行车,花了十几天把福州城走了好几遍,“连哪里有公厕都一清二楚”。
50多岁的罗光灿算得上是第一代小吃业主,2004年跑到北京开店,花了半年时间、走坏三双鞋,才找到一家心仪的铺面:30多平方米,以前是个蛋糕店。但办营业执照时,他才发现被中介坑了:签约的“房东”其实是个“三房东”,这导致他们无法立即办理营业执照。
在外开店,受委屈是经常的事。有一年在宁波开店,有个客人要求张万泉把辣酱送过去,当时正值午饭高峰,张万泉忙不过来,这位客人就把点好的拌面倒扣在桌上,还把硬币扔到厨房玻璃门上。“那种委屈感,很让人难受,没办法,得忍着。”张万泉说。
“小吃产业就是因为沙县人‘实说实干、敢拼敢上’才走了出来,吃不了苦的人干不了这个。”黄福松感慨道。
“攻城略地”有妙招
即便面临重重困难,沙县人出去开店的热情也不减,闯出了一条路。
“首先就是要打出声势,快速扩大市场,还有一个打法是农村包围城市。”张昌松大手一挥,俨然一副传授开店秘诀的老师傅的样子。他从2000年开始跟着堂哥出去开店做小吃,此后经常扮演沙县小吃“先锋官”的角色。
他回忆说,本世纪初有很多沙县人走出福建去开店。一个常见的做法是,几个相熟的老乡结伴到某个新城市,各自盘下一家门店,做同样的装修,约好同一天开门迎客,还搞起了同样的促销优惠活动。“为的就是让当地人突然发现,沙县小吃好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这样才能打出声势。”
“在同一个县城开了新店,等到时机合适就转给其他老乡去做,我们一般不会超过半年。”张昌松眯缝着眼睛,回忆起昔日的“开疆拓土”,“合肥那一片基本都是这么做出来的”。
靠着这个办法,沙县小吃快速“攻城略地”,走向全国。2005年前后,张昌松回到沙县盖起了独栋小院。那几年,他家的门槛都快被踏破了,来的都是想接手小吃店的人。
这些先走出去的从业者,不光转门店、教经验,还当起了沙县小吃的“天使投资人”。
80后卢佳敏早年跟着亲戚出去做沙县小吃,一家人在2006年就挣下了十几万元。听说这门生意挣钱快,堂姐也想跟着入伙,还提出一个全新的“盘店”想法:卢佳敏把小吃店转给堂姐经营,但可以保留四成股份,以后每个月都有分红。
“先试试看吧。”卢佳敏想。出乎意料的是,之后几年她每月都有上万元的分红。尝到甜头后,卢佳敏就一边自己开店,一边投资入股,2009年之后索性不再直接参与经营,转向专门投资,带动更多老乡投身沙县小吃。
随着沙县小吃的扩张,这些“天使投资”也顺利出海。前几年,有个在柬埔寨开沙县小吃店的堂弟找到邓方树,想找他借钱开第二家店。考虑了一会儿,邓方树提出改为投资入股。“这样解决了你眼前的问题,有钱大家也能一起挣。”说起那次投资经历,邓方树还颇有些得意。
但这些“天使投资人”也不是见沙县人就投资的。有一回,有个亲戚想入伙开店,希望能从卢佳敏这里拿到投资,卢佳敏就去他家吃了顿饭,发现这人家里厨房脏乱差,手艺也很一般,就果断拒绝了投资。“我投资有一个原则,最重视的就是这个人靠不靠谱,是不是够勤快、够机灵,做的东西干不干净。”卢佳敏说。
市场与官场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随着越来越多沙县人走出去开店,沙县小吃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但刚进城的许多沙县人仍然缺乏经营店铺的经验,有些人连账目都算不清楚,因此还闹出过不少笑话。要想让农民变成店主,甚至变成“做小吃生意的企业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沙县小吃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鑫还记得这样一个场景:本世纪初,他拉上几个率先走出沙县开店的小吃业主,抬着鸳鸯锅和小吃原材料,挤在一辆吉普车里,挨个村走访。每到一个村,就召集村里的年轻人来开会,请小吃业主介绍出去开店的经验,并现场演示各种小吃的制作技艺。
一个个开店致富的故事启发着沙县人,但这还不够。培训结束,张鑫会拿出一本“开店手册”,里面几乎囊括了做沙县小吃相关的所有事情,大到如何选址、办执照,小到店里洗手台该怎么设置,出去开店要在哪儿坐火车,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拨打哪些电话,这本“开店百事通”般的手册几乎无所不包。“让他们有对标的典型,有办事的方法,就能勇敢走出去了。”张鑫说。
但沙县人发现,有些外地人也在挂沙县小吃的招牌,有时连沙县本地人都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有些业主刚出去开店,就遭遇强买强卖:有人背着一大袋面粉霸占店铺门口,要求高价收购,不买就砸店、堵门。有时,在人流密集的地段,扎堆儿开了好几家沙县小吃,大打价格战。“这损伤的是沙县小吃自己的品牌。”黄福松说。
为护航沙县小吃这门“小生意”,沙县政府支持设立了两个办公室:一个是沙县小吃业主维权办公室,负责寻求外地公安部门的帮助,解决外出开店的沙县小吃业主普遍反映的强买强卖等问题;另一个是商标品牌维权办公室,负责申请和管理沙县小吃的统一商标,引导数万家沙县小吃门店错位发展,避免低端无序竞争。
发展到今天,沙县小吃已形成240多个品种,全县有数万人外出开店做小吃。有研究者称,沙县小吃创造了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奇迹、把草根美食转化为现代产业的奇迹、农民进城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奇迹。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闫龙跟踪研究过不少地方美食。他认为,沙县小吃的成功之处在于市场与官场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民间力量与政府力量的协同。“这并不是地方政府的原创,而是顺应当地产业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民间创业洪流与政府大力扶持的协作。”
“小吃二代”带来的变化
沙县小吃已成为沙县名片。据统计,2019年沙县农民人均年收入近两万元,其中2/3来自经营小吃店。县城里一半以上的房子都是小吃店业主买下的,当地还流传着一句话:“扁肉是砖头,面条是钢筋,炖罐是水泥。”
但用很多店主的话来说,沙县小吃“挣的都是辛苦钱”,“是用亲情和健康换来的”。包饺子、做扁肉、炒菜、捞面、炖罐、洗碗、送餐……店里样样事情都要自己做。清晨五六点就开门营业,忙到深夜一两点才休息,这是许多沙县小吃店的常态,甚至在南方的一些城市,还有24小时营业的小吃店。曾经,不少小吃店从业者忙到深夜,算账时“经常数毛票数到睡着”。
“乡亲们富了,但不少人身体也累垮了,有的甚至倒在了灶台上。不少年轻人不愿意再受这种苦。”张鑫说。
1998年出生的郑凯是标准的“沙县小吃二代”。从他记事起,父母就辗转东莞、深圳等地做沙县小吃。狭窄的店面通常临街,来来往往的客人多得几乎没地方下脚,晚上睡觉得猫着腰,才能爬进店内搭的小阁楼里。
2015年,郑凯顺利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回到沙县政府部门工作。得知消息,郑凯的父母高兴坏了,庆幸孩子总算跳出了“小吃门”。
但对于大多数沙县年轻一代而言,小吃依然是就业时的首选。根据沙县的调研统计,现在做沙县小吃的主力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不过,这些接过父辈生意的年轻人看得更长远。“做什么工作,得有面子也有票子。”张鑫说。
前两年,在北京打拼了十几年的罗光灿回到沙县老家,把北京的店铺全权交给儿子罗京经营。这原本并不在他的计划中。2008年大学毕业后,罗京跑到北京求职未果。第二年,罗光灿索性让儿子接手他在北京的小吃店,从最基础的点菜、做饭、收银一步步学起。过了两年,看儿子管理得有模有样,罗光灿便投资70万元,给儿子新开了一家门店。
如今,罗京已经把店铺扩展到了天津、保定等地,还在自己名下注册了独立的餐饮品牌。这让罗光灿颇为得意:“可能大多数(沙县)人都还没这个意识。”
张闫龙跟踪研究了沙县小吃的发展历程,在他看来,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小吃二代”对沙县小吃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原来是全部靠自己去做,现在的年轻人觉得需要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平衡,沙县小吃也要升级。”
近2000家门店接入了沙县小吃系统
作为“小吃二代”,卢佳敏明显感觉到,2014年沙县小吃走到了发展的拐点,“传统办法做不下去了”。店铺租金每年都涨,沙县小吃利润空间越来越小。黄焖鸡米饭、重庆小面、驴肉火烧等其他小吃也蜂拥而至,沙县小吃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
“最关键的还是消费者对餐饮环境的要求在提高,而以前大多数沙县小吃还处于脏乱差的状态。”卢佳敏说,很多沙县小吃从业者都急迫希望改变这个局面。
2017年,中华小吃产业发展大会在沙县召开。中国餐饮产业研究院院长吴坚在会上提到了一组略显尴尬的数据:食客去沙县小吃店消费,选择最多的菜品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粉面类、饭类和扁肉,其中名列第二的饭类并不是沙县特色小吃。另外,大多数顾客选择沙县小吃的原因是价格低廉,而顾客选择其他小吃大多是因为口感,而不是价格。
沙县小吃早已从旮旯小巷走到大街酒楼,可依然改变不了在顾客心中根深蒂固的“低端”印象。为推动沙县小吃产业升级,沙县政府从2015年开始搭建一体化管理平台,并开始对小吃产业进行数字化改造。
首先要改变的就是生产方式。按照传统做法,每一碗馄饨、蒸饺都要由店主手工制作,很多“小吃一代”起早摸黑准备食材。如今,在一些全自动生产线上也有了沙县小吃产品。
在沙县小吃产业园内,每天都有大量食材经过清洗、切碎、搅拌、调味等程序,被机器擀好的面皮包裹,变成一枚枚洁白又透明的柳叶蒸饺。经过零下40摄氏度的螺旋速冻装置后,这些蒸饺又“跳跃”到包装袋里,被送上运往全国各地的货车。几乎每天都有20吨蒸饺,像这样从沙县配送到全国各地的沙县小吃加盟连锁店。
近年来,沙县成立了国资背景的沙县小吃集团,在全国各地建立多家子公司,加盟连锁门店统一标准、统一形象、统一供应链,共有近2000家门店接入了沙县小吃餐饮连锁供应链服务系统。借助数字化等技术,沙县小吃也在变得“高大上”。
邓方树是最早的加盟连锁店主之一。在他的店里,店面装修、服装、餐具都是统一的,菜单、招牌都是小吃集团统一提供的,连豆浆机都比市面上的便宜很多。“我们作为第二代还是挺享福的,后面有这么大的一个集团和政府在给我们做支撑。”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主打堂食的沙县小吃经营业绩直线下滑,许多门店关张。沙县小吃同业公会发出倡议书,号召全国的沙县小吃店铺房东减免一定数额的租金。沙县县委书记杨兴忠以个人名义,向美团网发出了一份求助信。沙县还出台了支持小吃业主共渡难关的十条措施,其中沙县农商行紧急提供3亿元授信。沙县小吃集团也减免了所有加盟店管理费。
原本主打堂食的沙县小吃也开始重视外卖,研发了更适合外卖的新产品。“以前翻台率很高,压根儿没时间做外卖,今年因为疫情开辟了新战场。”在张鑫看来,沙县小吃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不光开店速度非常快,即使有疫情影响也能很快恢复。“每一个沙县小吃都可以成为沙县人东山再起的据点。”
如今,只有27万多人口的沙县,有6万多人在从事小吃生意。种植养殖、加工销售、物流配送、数字化服务……沙县小吃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全产业链。2018年,全县食品产业产值超80亿元,带动了物流、餐饮及旅游等第三产业增长。
在沙县,很多人都有个共同的“小目标”:把沙县小吃做大做强,让沙县小吃也能诞生上市公司。也许到那一天,曾经背着木槌、鸳鸯锅四处打拼的沙县小吃业主,就会有一个崭新的身份。